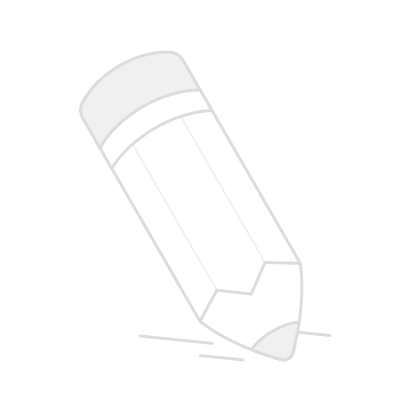散文【为了一个并非渺小的理想】作者:张敏
披一回人皮做上一回人,来到这个世界上,稍稍懂事时,便知道不能随地大小便;再大些,便会想到,自己这辈子,靠谁来养活?自己又要养活谁?倘若是一个脸蛋很漂亮的女孩儿,大人们便说,这妞儿将来定会吃香喝辣。那香那辣从哪里来?这罪孽肯定要落在一个男孩的头上。
有幸生成一个男人,夺天地阳刚造化之功,上马挥刀夺天下,安定社稷;下马进家,给老婆孩子挣吃挣喝,方才是男儿本色。
理想对于男人来说,犹如一匹马的四条腿,犹如一条龙身下的云和水。
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我和几个都是十七八岁的新兵,在营房后边的砖瓦窑上谈起了个人的理想。热血沸腾之余,我们把自已的名字写在一块砖头上,向上苍发了誓,然后把砖头砸得粉碎──谁要是说话不算数,下场就和这砖头一样!大家都说了些什么理想呢?
有两个战友说的理想是下决心存钱(那时我们在青海香日德当兵,每月有五十多元的津贴)。如果当五年兵,每年存五百元,退伍便可存到二千多元。那时候,钱顶用,二千多元是个很可观的数目。有一个战友要拉二胡,说将来最起码要在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为大家演奏。还有一个战友说,他要搞音乐创作,最少要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首自已创作的歌曲。
轮到我时,我说我要当文学家!要写一个电影剧本,要在银幕上看到我是个编剧。然后再写十篇小说,全要用铅字印出来。
这里面,数我的理想最伟大。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,我的心跳得很厉害。
如今,三十六年过去了。当年,名子写在砖头上的那几位战友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。有一次遇在一起,自然谈起了那场“砸砖立誓”的事,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。
存钱的,临退伍时存到三千元以上。为了存钱,他们有几年都是用指头蘸盐刷牙,省下了牙刷和牙膏钱。不过现在并不怎么富裕,因为那些钱都花完了。他俩说,三千元是个狗屁,现在一条狗都值三千元。
拉二胡的那位,果然在他们工厂举办的千人以上的晚会上,上过两次台,也确实得到了掌声。
早在1965年,那位搞音乐创作的战友就在《解放军歌曲》上发表了一首队列歌曲。只是现在不搞了。原因是有一次看到一张雷振邦的工作照,看见雷大音乐家的身后挂着许多乐器时吃惊地说,咱搞什么音乐创作哟,那乐器连名子咱都叫不上来。
这其中,唯我最苦。那次砸砖起誓之后,我便一个心眼写电影了。我的职业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押犯人。这里没有新华书店,也没有图书馆。我手头只有一本《电影文学》,还是别人到格尔木开会时给我偷来的。我反复看了几十遍,便开始写一个《岳飞》的电影了。因为参军前,我看过《说岳全传》,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书。便根据回忆,把神和鬼搅在一起,去写岳飞了。刚一动笔,就恬不知耻地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信,报喜似的,说有一个青年战士在写《岳飞》的电影了,请作好拍摄准备。二十天后,我收到了八一厂文学部编辑寄来的一封信,信中告诉我《岳飞》已有人写过了,作者叫陈荒煤,是位著名的艺术家。不过,看到我的信,他们很高兴,在电影创作的大军中又添了一们战友。信中让我从生活出发,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。我把这封盖着公章的信象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倒背如流,信也成了破抹布。
我当兵的那地方,是黄沙包围中的一个小农场,除了几千名犯人,就几十个管教干部和一个连的武装。没有飞鸟,也没有女人。一年最多能看三场电影,轮到上哨时还看不成。报纸有两份,锁在指导员的抽斗里,不开会学习,通常是见不到的。《岳飞》写不成,剩下的电影剧本怎么写?电影剧本写不成,我想到了那块被砸碎的砖。
有一天,我到监狱里去,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犯人正在画一幅监狱里开晚会用的大布景,我随便看了看,指着那布景的右下方说,这地方调子是不是太冷了?我上过一年多美专,才说出了这一句行话。那老犯人立刻用惊喜的目光看着我,激动的说:“报告班长,你是个内行呀!”对待犯人,我是不屑一顾的。那时候,阶级斗争天天讲,时时讲。部队教育我们,每一个犯人,就是一名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。他竟然觉得我们当兵的没内行,岂不是小瞧了我们?于是便神气地说,冷暖调子谁不懂呀!你逮捕前干什么?
“报告班长,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!西画系的。”
这下轮到我吃惊了!中央美术学院的西画系教授?我参军前在学校里,请刘文西来讲一堂课,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个星期。刘文西那时候才是个讲师。看他那颤颤巍巍的样儿,竟是一名西画系教授?还是中央美院的?再一问,他说他在意大利留学十七年,学成回国的。我让自己镇静下来,坐到火盆前,也让他坐下来,掏出一盒上海牌香烟,丢给他一支。他接了烟,把烟横在鼻子下边,贪婪地闻了一遍又一遍,舍不得点燃。他说,他好多年没闻过这烟味了。我换了一种语调问:“你犯了什么法?”
他立刻站起来:“报告班长,我是极右分子,刑期十五年。还有十年。”
我没有问他叫什么,只问了他家里还有什么人。他说什么人在美国,什么人在英国,我全不感兴趣,最后说了一个人,是他的小儿媳妇,叫陈曼倩,在《电影文学》当美编。
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脑子里亮了一下。我记起了,我那本唯一的《电影文学》杂志中,有一个电影剧本的插图作者就叫陈曼倩。
我问清了姓名,立即返回营房去查我那本《电影文学》,果然不假,提笔便给她写了一封信。告诉她,我在监狱里知道了她的名字,希望她能替我买一些电影文学之类的书。半个月之后,我收到了这位大姐的一封信,行文心照不宣,希望我能给予一些“照顾,”并答应替我购买一些书。我当即寄上了三百元。一个月后,我收到距我四十公里外一个邮电所的通知,说有一大批邮件,让我设法领回。我 牵了三匹马,驮回了一公尺高的六叠子杂志。那些书刊杂志解开来,足足有一个立方。..
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