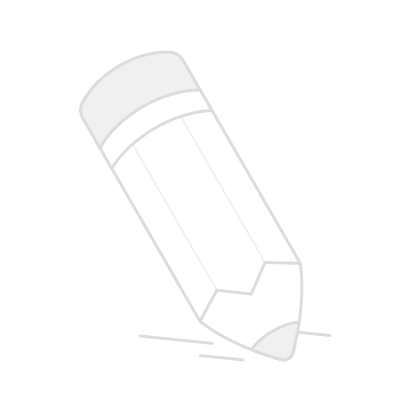<span><span>文/没头脑也很高兴</span><br /> <br /> 我可能是病了。</span><br /> <span>可是我在我身上找不出一道伤口。</span><br /> <span>但我相信我是病了,我头有点疼,嘴巴有点苦,想写点什么,手指头却像水泥粘着一样僵硬。我想,那我说点什么,我张大嘴巴,像活死人一样,从喉结发出“嗬——嗬——”的声音,可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。我想说点什么呢?我费力的想组织语言,却发现身体,每个关节连着组织液,都闷疼的不得了。就像一万只蚂蚁钻进你的肌肉里,淌进你的血液里,有血液在你的血管里奔腾,暴躁的冲撞着皮肤,来来回回。</span><br /> <span>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吧,把所有的厌世、消沉情绪,都怪罪到生病里,生病是一把很好的保护伞,不想和他人接触,想躲在一个人的世界里,就告诉他人一声:“我病了”。或者,干脆,谁都不告诉,静静的把门帘拉上。窗外,雨脚打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上,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影在积水里被车轮驱赶的来回激荡,四处飞散。从斜拉的窗帘缝隙里,看到雨雾一层层蒸腾起来,人就像隔绝在浮云里的仙人。</span><br /> <br /> <span>人有时候会怀念生病,生病就像挖战壕,会检验一个人在喧嚷而冷酷的世间独自作战的能力。一个人撕开药包,把药粉洒在杯子里烫上热水,喝下;一个人去诊所打针,针头扎进青紫色的血管里,在他人有家人相伴时倚着椅子装睡,闭目养神;一个人爬起身子,冲泡面或给外卖打电话,在门铃响起时挤出感恩的笑容,再慢慢的挪回热气已渐散的被窝里;一个人听歌,在歌里找些共鸣的情绪,怀念一些错失的人;一个人,擎着手机,在长串的电话簿里犹疑,却最终放不下骄傲和独立,把手机扔进书摞里;一个人,咬着嘴角,忍受着疼痛的折磨,却自虐的贪图着短暂的清净坚忍……</span><br /> <span>生病是我们唯一要公平面对的事情,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,不论你睡的是席梦思还是铁板床,病症很公平的突降到你身边,就像一个表面乖顺的野兽,悄悄的蹲在你的床脚,在你完全不设防时张大血口……你脑子里那些关于爱情啊、房子啊、工作啊、人际啊的抉择在生病面前不堪一提,尽管还是有少部分的人,会在自己已累成散沙时,还拿他人的琐事来烦自己。</span><br /> <span>生病有时会是欣慰的休憩,它提醒你,你已为他人的事情费心太多了,该好好琢磨下自己的事情了。看看自己头发白了没,眼角的皱纹多了没,上一次给自己煲汤,做一桌饭菜犒劳自己,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。</span><br /> <br /> <span>若是病在器官上,还不太严重,科学发明了无数的药丸:睡不着,有安眠药,疼,有止疼药,累,有葡萄糖,这些大大小小的药丸,汤液犹如家仆,侧身人旁忠心不二。难以治疗的,是心里的病,那些藏进心脏,想让他人看出来又看不出来的心病。</span><br /> <span>在喧闹的聚餐里,忽的就不想说话了,静默地凝视着窗外,白杨树的叶子被晚风揪下,在风里孤冷的打着圈,烤红薯的老头双手揣进袖里,暖烘的光火照亮他微皱的鼻翼。赶车的年轻人在车站前,低头把玩着手机,排着安静的长龙。血红色的灯光从酒吧、店铺、饭馆里流泻出来,车子就像移动的骨架,把一个又一个“僵尸人”移送到始点和终点。没有繁星密布,只有黑云覆盖了远处离散的屋舍……呵,忽然就难受了。忽然就质疑自己在一桌人里像模像样的端着酒杯,说着冠冕堂皇的祝酒词的意义:我为什么来到这陌生的城市的?为什么要坐在这里?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疲惫不适统统的掩藏起来?</span><br /> <span>城市不允许你有丝毫的质疑,它严格的筛检着你的情绪,把脆弱啊、迷茫啊、伤感啊,统统都筛出去,然后剩下克制、容忍、服从、归顺等情绪,捏出一个在城市喘气的你。你忽的有些想念乡下的牛群了,弯长的睫毛上,有露珠冻成的冰霜,牛尾悠闲的拍打着蚊蝇。白纸砌成的炕头上,有你盘着腿的一颗一颗搓玉米的老父母,灯泡晃亮的厨房里,有妈妈手温拣过的大米饭和甜香的红烧肉。</span><br /> <span>乡愁是一种病,一种听到乡音就会得,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就会发作的病。</span><br /> <br /> <span>那个常在绿茵场里和你踢球的哥们,如今已是2个孩子的爸爸了。自上次见到他,已是半年前了,他开了公司,忙的头慌心乱,你提出再去大学里踢场足球,哥们尴尬的推推手,捏起啤酒肚,依旧满嘴没溜:以前是我踢球,现在换球踢我啦!你干干的笑着,头顶上的风扇一圈,又一圈的旋转着,你忽然想到了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——两只在天花板顶上,一天,又一天结网的蜘蛛。在KTV里点着少年常唱的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,三五个老爷们勾着肩膀,一打啤酒灌肚,唱的声嘶力竭,却再也唱不出过去的意气轻狂。虽然就在一座城市里,可公交、地铁和二、三环的划分阻断了老友的相见。谁说只有爱情世界里,才存在——最熟悉的陌生人呢?</span><br /> <span>多想回到过去,穿上机车服,骑骑摩托,在新鲜的草地里跑一跑,摔一摔,然后和哥几个夜聊到深夜啊。如今我们不再在草地里摔跟头,却在商海里跌爬滚打。如今我们不再弹吉他,见面必谈赚钱计划。如今我们能买得起一瓶几百元的红酒,却再难喝出凑钱买啤酒的潇洒。</span><br /> <span>晚熟是一种病,一种起早贪黑,累断筋骨,却在走过大学的校园时,忽的就悻悻然鼻酸的病。</span><br /> <br /> <span>“有次,我用光了所有的表情,在人群中仓皇而逃。”</span><br /> <span>有阵子,我很害怕和人接触,人的双眼就像X光机器,任何虚假的东西都逃不过它的透视。我们惯于对他人的生活捕风捉影,却对自己的生活得过且过。吃速食、睡在邋遢的床铺里、在一副又一副干净或不干净的胴体旁游走,换一个又一个职场属性。我们希望别人了解我们,所以发微博,聊陌陌,可又严防隐私,怕某天被要挟或中伤。可人又很聪明的去装傻充愣,明明看穿了却佯装看不明白,以此维系薄弱的情感。我有天看电影,忽然想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惯于装傻的社会,人人都在装傻子,因为只有傻子才不叫人设防,清醒逼得我们困惑,失望到直想脱身而逃,该有多可怕啊!你不知道那个经常和你打招呼,冲你笑的甜蜜蜜的人是真的喜欢你,还是礼节的讨好;你不知他说爱你,是真的爱你,还是仅想和你鱼水之欢;你不知别人说的“有事找我。”是真心帮助还是下一秒即忘的敷衍;你不知道,那些软弱无力是真的脆弱还是乞怜骗钱的戏码……这你现在所睡的,睁开眼睛就要面对的世界,有多少是真的部分,多少是装傻充愣的部分,还有多少,是自作聪明实则人人都能看穿的部分。</span><br /> <span>幽默的人或自以为幽默的人越来越多,可这幽默感里,参杂着多少的悲剧感?多少人由于对现实的纷扰感到无能为力,而不得不保持缄口不言?</span><br /> <span>沉默是一种病,一种用沉默来对抗虚伪,不站队也不掉队的倔强和无力。</span><br /> <br /> <span>“我们都被困在了自己的身体里……什么都不剩,我们只能看到周围的世界是如何乱成一片。我们都一样,都能感觉到苦痛,生活中都有混乱的部分,生活本身就使人相当困惑,我无法得出答案,但我知道如果你将它写出来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</span><br /> <span>电影《超脱者》里,男主角如此回答一个患有节食症的向他发问的肥胖女孩:你看,如果你将它写出来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</span><br /> <span>我沉默着,蹲坐在黑夜里,指头僵硬的打字……外面不知谁家,点燃了鞭炮,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划破了寂静。喜事,白事,又有谁在乎呢?至少于我这个听众,是不在乎谁家多了一桩喜事或悲剧的。窗外的街上,依旧有一辆辆出租车从积水里驶过,依旧有行人沿着一条街向一条街走去,依旧有年轻人嚎啕寻醉,老年人捡拾着塑料瓶子……地铁上,有某个人斜靠着晃荡的车体,并列两侧的人们,疲倦的点着头补觉,就像在集体赞同着什么。穿过隧道了,隧道里静的什么声音都听不见。几分钟后,他在信号灯的提示下,一个接一个的与人艰难地调换着位置,甩开步子走出了车门,消失在黑影幢幢的楼群里……<br /> <br /> </span>